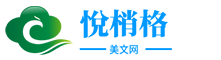【摘要】贾樟柯电影具有“站台”式的艺术视角,记录着芸芸众生悲欣交集的一瞬,省略着漫长的人生过程,这种风格在电影《站台》中具有了极富代表性的体现。通过《站台》中的人物可以看到贾樟柯是如何以貌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的客观记录,最终实现他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站台青春普通人追忆
一、引言:站台视角和关注人群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固定的站台上,火车呼啸而来,小停片刻便又绝尘而去。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人流熙熙攘攘,片刻之间便相聚和别离。出发和回归。站台,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场所。“站台”上的追忆,往往是对刻骨铭心的往事一种达观的回望,是对纷纷芸芸生活琐事饱含情感的梳理。在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的《站台》中,贾樟柯正是用站台般的艺术视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山西的一个县城里,不为人注意的青年们那匆匆流逝的青春韶华。
青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80年代初,刚刚20出头的余华曾经是一名牙医,生活因为不得不“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8个小时”、“观看了数以万计张开的嘴巴”而变得“无聊至极”。“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而进入文化馆的生活在余华看来也单调地沦为站在窗口看着院子里那株秋日的梧桐,他“仿佛看到以后的一生将这样度过”,于是产生了去北京闯荡的念头。同样,对于山西县城文工团里拉二胡的崔明亮等众多青年人来说,来自北京的广播新闻,来自广东的流行音乐,来自夜空下孝义市那星星点点的灯火,以及象征着远方、未来和希望的火车,都因为带上外面世界的光彩变得神圣而美好。对于美好未来的期待和对于外部世界的期待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成了山西县城里所有年轻人的心头大事。《站台》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曾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与作家余华成功让梦想变为现实不同,贾樟柯艺术视角所关注的是一些最终没有迈出故乡、湮没在时间岁月长河里的失败者、平常人。在其随笔《假科长的你买了吗》中,贾樟柯这样阐述他所关注的对象:“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犹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俗,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春妮的周末时光 何云伟 应宁 王玥波 离婚,但他们放弃了。……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l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在贾樟柯看来,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才是支持这个庞大社会前进的主流力量,而媒体对于这类人群的关注远远少于对成功者的赞美。于是,成功了的贾樟柯将手中的摄影机转向那些曾经伴他左右、一起放飞、但最终没有同他一样实现梦想的伙伴,用这种关注的目光“去挖掘和展现人民之中蕴藏着的进步的力量”,实现他对社会的思考,对底层人群的关怀。贾樟柯以《站台》为主题曲并以此命名电影,不仅因为它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更因为《站台》的歌词:“长长的站台,长长的等待,站台会带着人们追逐梦想,站台会承载人们归来的疲惫”,隐射着那个年代大多数有梦想但最终没有实现梦想的青年的客观状态。而在电影中,贾樟柯饱含着最大的敬意,追忆、记录、思索了那一段放飞青春、回归庸常的似水年华。
二、“站台”上的人物
1、尹瑞娟篇
在对尹瑞娟的描绘中,贾樟柯运用“缺失”的结构表现这个女性尊严。
尹瑞娟是县文工团员,却不像崔明亮、张军等一般文工团员那样爱自我标榜,用喇叭裤、红棉牌吉他等外在的东西作为彰显自己“文艺”身份的光环,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也没有钟萍那般果断大胆、无所顾忌,对其所爱奋起直追,将与张军组成家庭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尹瑞娟有着青年人压抑不住的青春冲动――她不顾父亲反对喜欢崔明亮,她好奇新鲜事物《流浪者》上映,她去看:张帝的歌流行,她去听:抽烟时兴,她去学。她是一个有些文艺细胞的姑娘――既会在《姑苏行》的配乐中抑扬顿挫地朗诵《风流歌》也会在空无一人的房间翩翩起舞,她的照片还会被长期放置在照相馆的橱窗中招揽生意。然而她更是一个冷静务实的人,决绝地将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因素从生活中一一去除;她喜欢崔明亮却主动提出分手,理智地要求和崔明亮保持朋友关系,因为在他身上看不到前途;她喜欢激烈的流行乐,至多也只是坐在一旁,为在疯狂的蹦迪节奏中陶醉的人打拍;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拒绝漂泊不定的走穴演出,而是想通过考进省艺校为人生寻找更大的舞台。冲动和理智并存构成了这个人物的尊严。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尽管她对自己有着冷静的规划,对人生的梦想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小小县城中,她的青春理想渐渐被湮没――她想通过考学继续艺术之路,最终却成了一名与文艺毫无关系的税务员。她想嫁入有着更好社会地位的家庭,最终却只能与一直没有看好的崔明亮成了家。她想离开县城为未来寻找更大发展空间,最终却守在县城一个给她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岗位上,开始日复一日的生活。
对于这些生活中重大转变的,贾樟柯一律将其推向幕后,对尹瑞娟的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的走穴演之后,出现大片空白,最终在演出队解散崔明亮回到汾阳后,得以重新出现。贾樟柯不去展现尹瑞娟未被省艺校录取的沮丧失落。不去展现始终没有成功的若干段恋情对她的挫折打击,也不展现她选择放弃金色的艺术梦想、过一名普通人生活的落寞。贾樟柯只记录独自一人的尹瑞娟,晚上在冷清办公室听着广播里流行歌《是否》突然独舞起来的激情,以及白天又穿着税务员制服,骑着摩托穿行在县城街头的平静:只记录年轻时小动作不断,讲话时眼睛不敢直视崔明亮的紧张,以及十年之后神色坦然,话语间面带微笑观察对方的自如:只记录徘徊在张军家外、自家走廊上,想等到一个和恋人单独说话机会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矛盾,以及结婚后抱着孩子不停地轻声细语,却与丈夫懒得沟通的漠视和淡然。贾樟柯对这个要强却没有成功的人物保持尊重,让观众去体会去猜想这些生活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用空缺的神秘代替现实的残酷,使得出现在镜头前的尹瑞娟始终不温不火,不骄不躁。正如贾樟柯所说“我电影中的每个人,他们在大同,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让别人了解过,他们保持着尊严,绝不煽情。”。正是这样省略转折、表现转折前后个人状态的记录手法,让贾樟柯实现了他的目标:“我也想让我的电影有这样的品质。”
2、崔明亮篇
崔明亮喜欢阳春白雪的尹瑞娟,但在要强的尹瑞娟面前一点却不肯放下架子表示主动,至多只是在远处默默欣赏。当尹瑞娟告 知他自己要去相亲时,崔明亮的无所谓装得生硬;当尹瑞娟主动提出分手时,崔明亮的潇洒装得决绝;当若干年后,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崔明亮第一次受到邀请去尹瑞娟家做客,话语问无意流露出对尹家摆设的熟悉程度。方才暴露自己当年在城墙上的默默遥望究竟在心里烙下了多深的痕迹。
崔明亮当年对爱情的美好想像并没有实现。在走穴演出几年之后,崔明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伴侣――新入团的女演员小娥。小娥没有尹瑞娟清高,却能给孤单的崔明亮带来安慰。贾樟柯只用了三个细节表现他们的关系――一个长长的横移镜头中,老宋叫大家起床,掀开被子的一角时,崔明亮的头和小娥的头在一个枕头上,镜头很快掠过俩人,继续滑向别人;在等车时,处在逆光角落里的崔明亮枕在小娥的腿上打盹;在演出队解散之夜,歌房里狂舞的人群中,崔明亮抓起小娥的手,离开众人,将她拉到景深处的门帘后。短短三个细节,隐藏在长镜头的景深中,不动声色地告知了观众当年曾经追求阳春白雪式爱情的崔明亮,被时间改变不得已而接受平庸恋人的事实。
后来,崔明亮回到县城,发现昔日的恋人尹瑞娟仍然独身,而且对方主动发展与他的关系。被时间改变的崔明亮终于与尹瑞娟结婚了,只是当年的期望不再,失去了对爱情美好期望的婚姻只是一个为了生活而生活的躯壳,崔明亮在这个躯壳中进一步接受了生活的平庸。贾樟柯把崔明亮的结婚过程隐去,只记录结婚这个时间点前后的生活片段――婚前在尹瑞娟家门口吸烟以及婚后在妻子家沙发上午睡的崔明亮。
对崔明亮的表现手法体现了贾樟柯一向推崇的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强调在完整的空间里尽量观察人的存在”。用长镜头大段大段记录崔明亮追求、妥协、包容和享受,表现出崔明亮的改变是无奈的,但正是这份改变,使得崔明亮心态平和地成为万千普通人之一。否则,一直追求阳春白雪只能使他走不出对尹瑞娟的思念,找不到寄托感情的实体;而一直追求外面世界的虚无飘渺只能使他更加漂泊不定,找不到家庭的稳定;一直追求想象中美好生活只能使他无视眼下的现实,找不到脚踏实地的方向。正是不断的妥协春妮的周末时光 何云伟 应宁 王玥波 离婚,才使得这个年轻时有着美好追求的人,在并不美好的现实中也能不断地自我满足。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如果说,梦想是他年轻时前进的最大动力,那么。妥协就给了中年的他面对现实最大的勇气和韧性。贾樟柯记录在妥协中过活的崔明亮,成为千千万万个曾经有过梦想的中年人的生活写照。在长镜头中的崔明亮身上,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观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3、钟萍篇
对自己所爱主动追求是钟萍的人生信条。
为了和自己爱的人张军在一起生活,钟萍受了两次伤害,堕胎以及被公安局以论罚。两次伤害,张军的懦弱和不负责任没有变化,钟萍的反应却大不相同。第一次,贾樟柯表现了以稳定至上为带团方针的文工团徐团长的包容。徐团长为丑事保守秘密,寻找对策,把两人从遍地熟人的县城带到偏远农村偷偷手术,以此息事宁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前一个县城文工团长淳朴的处事策略。第二次,钟萍张军又出了丑事,老郑被警察局喊去领人认错。老郑将两人从无人认识的吴堡带回了县城。领去的是乡村,带回的是县城,对比反差强烈。贾樟柯并不记录小镇上的流言蜚语,把老郑如何处理这类丑闻推至幕后。他只让观众看到一去一回的对比,只看到老宋当街大骂钟萍不遵从演出队的走穴安排的粗俗,只看到张军无言面对钟萍那沉默父亲的落荒而逃。贾樟柯记录的只是重大转折前后的蛛丝马迹,把真正激烈的冲突过程一概抹去,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审美效果。显然,赚钱至上的老宋对钟萍不会抱有怜悯,甚至在他看来,钟萍的话题可以成为增加他团长影响力、在茶余饭后拿来显摆的谈资。作为钟萍最亲近的人,张军对钟萍的离去负有直接责任却不愿也不敢承担。这使得钟萍声名不保,她对这个世界单纯的信任直接转变为深深的失望,才会做出离开的选择。
钟萍没有屈从于这个改变她命运的县城,她去了异地他乡寻找能够让自己的信条得以生存的空间。钟萍的离开终以张军、崔明亮对她没有结果的寻找呈现,她以消失的姿态传达出贾樟柯对人情世故变迁的失望与苦涩,以及对热忱、纯洁这类珍贵品质的捍卫。
4、陶二勇篇
如果说以上几个人物带着贾樟柯自己和熟悉朋友的身影,那么陶二勇则像是一个当年不那么亲近的朋友。
在电影的上半部,二勇的出现多半是跟随着崔明亮和张军,作为一个配角现身。他存在的意义只是冲淡了观众对崔尹、张钟两男两女爱情故事俗套的质疑。在文工团解散,开始走穴演出后,二勇认为老宋带队没有前途,打算自己做小买卖养家糊口,没有跟随崔明亮等人一起闯荡,便彻底从故事中消失。
在电影的下半部,二勇在钟萍离开张军后,以在家没劲为借口,加入了老宋的走穴演出队,不久之后就和新入队的姐俩之一小娟走到了一起。于是,影片上半部在故土成双八对的崔明亮和尹瑞娟、张军和钟萍两对恋人,影片下半部被替换为在他乡卿卿我我的崔明亮和小娥、二勇和小娟。最后,当演出队解散,二勇又同崔明亮等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重新开始做起生意。他走穴时的恋情不了了之,开始了固守县城的稳定生活。一直到结尾,贾樟柯也没有给出二勇如何成立家庭等等答案。
对于二勇的人生,贾樟柯保持着不合理的空白。观众只知道二勇作为一个文工团员在县城里自由自在,文工团解散后又动起做生意养家糊口的脑筋,突然有一天跟随老宋开始了漂泊不定的走穴,最后又回到家乡做起生意。但是这些空白正符合贾樟柯追忆过程的真实性,因为个人的回忆局限于他的视角范围,他的视角只局限于他所经历过的和他能够打听到的事情。在影片上半部中,恋爱中的崔明亮与恋人男友张军关系比独身一人的二勇关系亲近,二勇的展示空间便远远小于张军;而下半部贾樟柯却给了二勇远远大于张军的展示空间,也因为张军的独身,脱离了与小娥恋爱的崔明亮的关注视野。二勇的存在与消失、出现频率的高与低完全是和贾樟柯的“追忆”姿态息息相关的。因此,二勇虽然不像尹瑞娟、钟萍、崔明亮那些主角那么出彩,却以合理的缺失,展现了一般电影中配角不存在的真实感。
三、结语
贾樟柯电影“站台”式的艺术视角,产生于他自小形成的一种异于常人的嗜好: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家乡的大街小巷。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日后成为他电影创作的素材来源,成为他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也许,正是贾樟柯在家乡汾阳小道上日复一日地行走,让他深深体会到“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在《小山回家》里,贾樟柯只记录因为丢了工作,爱面子的小山无颜回家前的焦躁,而终究也不表现见到父母时的小山将怎样为自己辩解。在《三峡好人》里,贾樟柯只记录沈红在拆迁的废墟中来来回回寻找丈夫要讨个说法的执着,而终究不表现因何做出放弃婚姻决定的那关键一刻。在《世界》里,贾樟柯只记录小桃和太生因为互相怀疑不断疏离,而终究也不表现这层裂痕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贾樟柯电影就像一个长长的站台,“没有来龙去脉,只有浮现在生活表面的蛛丝马迹”。让观众面对空旷的站台,面对贾樟柯电影视角下惯常省略的人物命运过程,展开丰富的联想,产生巨大的共鸣。
贾樟柯电影“站台”式的艺术视角,表现为用“长镜头”忠实纪录底层平民,直面人间世俗,探询真实的情感,同时不回避“人性的弱点”和“生命的感伤”,通过貌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的客观记录实现了他的人文关怀。因此,贾樟柯的作品才被人们称为“当今中国成功的国际文化品牌”。外国观众也许在经历了《红高粱》里民俗奇观带给他们的新奇后,通过贾樟柯的站台视角,在组成其电影主体的普通人身上,获得关于庸常和宽容的强烈共鸣。
来源【励志网】自媒体,更多内容/合作请关注「辉声辉语」公众号,送10G营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