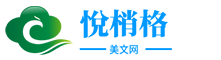一、鱼儿亲上我的脚
八九月的天气,夏日的余热还未散去,秋天已飘来一丝丝清爽。庄稼还未成熟,空气里飘散着糯糯的甜香。我踩着被秋阳拉长的身影,头上顶一个瓷实的瓦盆,站在村口的石碑上喊一声“抓鱼去喽”,就跟上来几双蹦蹦跳跳的小脚板,一路歌唱,绵延到小河的深处。
河水不深,能清亮亮地看见泥鳅钻出来,静躺在河床上晒太阳。水流也不急,可见三五鲢鱼条子逆流而上,游至浅处,阳光打了一下脊梁,才惊慌着一跃,优美地凌空转身落在水里,向深处游去,再也不肯露面。
锹不是特制的,大手握着上下翻飞看上去叫人羡慕,小手却憋红了脸才挖起一方小小的泥块。更小的手向泥水里一插,一把水淋淋的河泥就捂在了围堰上。“人多力量大”,“小”人多了力量也不可小觑,小小的身体被泥巴裹住的时候,一方低低的围堰已经圈住了鱼儿们快乐的时光。被挡在围堰里的鲫鱼板子、鲢鱼条子和扛着枪的“ge ye”(背部有刺鳍的一种鱼),仓皇地游来游去,直到累了,才停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无奈地望着天空。
风,沿着河筒子轻轻地吹。一群羊吃饱了躺在松软的河滩上休息,间或从梦中醒来,悠长地叫了几声,芦苇就飘出了云般的长缨,柔柔地荡来荡去,就是离不开小河的怀抱。
围堰里的小鱼此时大多忧伤地躺在瓦盆里,紧紧相拥,茫然对视,看不见自由的时光。芦苇荡里有草鳖,这是二叔说的。几个小影子大着胆子钻进了芦苇丛中,惊醒了一只尖嘴鹭鸶,扑拉拉向天空飞去。大约翅膀长得不够硬朗,没多远,就斜斜地落在一杆芦苇上,叽叽地叫,像在呼唤着远处觅食的母亲。
蛇般蜿蜒的是一条黄鳝,悠哉悠哉地游了过去,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呼。胆小的自是不敢下水,胆大的已绾起了裤脚在水底摸索着,不一会儿,准能甩上来一条二三两重活蹦乱跳的鲫鱼板子。
小小的瓦盆里像翻开了锅,透不过气来的鱼儿把嘴伸出水面,大口呼吸着秋天的气息。可能是最小的英子看瓦盆里的水实在浑浊,抑或是英子听见鱼儿们的哀求了吧,走到河沿,瓦盆一倾,全倒进了流淌的河水里。之后,反正英子是眼泪汪汪,万分难过地面对着一张张失望的小花脸,抽泣着说不出话来……
远远地听见娘的声音了,一声高一声低,沿着水面一路寻来。脚板子有些痒,一啄一啄的,“鱼儿亲上我的脚”,欢快地佯做惊呼了一声,撩起的水珠,满天晶莹。芦花荡呀荡,木棍敲起瓦盆响叮当,一个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小河的记忆里,渐渐远去……
二、 种我一生甜瓜香
瓜爷不姓瓜,但是爱种瓜,所以称为瓜爷。少不经事,常在瓜棚里问瓜奶长的什么样,瓜爷不说话,抓把烟叶塞进烟锅子,望着瓜田陷入沉思,仿佛那绿油油的瓜田里,满处都是瓜奶的影。
后来听前院的六奶说,瓜爷打没分田地的时候就种瓜,不过那时还很少种甜瓜。还说村里常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往瓜田里送饭 ,白白净净,惹得瓜爷的日子天天哼着小曲儿。“那是东庄的一个寡妇,出嫁半年男人就死在豫西的煤窑上。”六奶说起来眼里汪着泪水,“后来带着身孕,脖子上挂一双破鞋,满大街游行。终于有一天瓜爷在瓜田的水井里捞出了瓜奶。打那起,瓜爷就没再给队里种瓜,只身下了关东……”再后来,瓜爷就是我看见的模样。从关东返乡的瓜爷又承包了那块地,孤身一人,别的不种,专种甜瓜。
瓜爷说 :“她喜欢我种的甜瓜。”
初秋的夜里有风,瓜棚里的油灯闪烁着豆大的光亮。三五个娃儿被甜瓜的香甜拽住了脚跟,赖在瓜爷的瓜棚里不走。瓜爷喜欢小孩,月亮底下拣来一土篮熟透的香甜:“一人俩,别吃独食。”然后提溜着本不用提溜出来的豆大光亮,送娃儿们上路……
不管吃水,还是浇灌瓜田,瓜爷只用瓜奶栖身的那口井里的水。说来也怪,村子里不止瓜爷一人会种甜瓜,可别家种的就是没有瓜爷种的香甜。瓜爷也是,老旱烟抽着,苞米饼子就甜瓜,竟吃得面色红润。夕阳照着,金色的光芒照在瓜田里,一个个白生生、绿莹莹的甜瓜被涂上了一层油彩。瓜爷慢条斯理地摇着辘轳,清亮亮的井水被汲上来,欢快地流进瓜田里。瓜爷有些醉了,仿佛看见瓜奶的俏模样,愈来愈清晰,黑夜里,瓜爷肯定会走进一个甜暖的梦境。
甜瓜再甜,不如偷来的香甜。选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三两个小崽子,起着鸡皮疙瘩,从豆亮的暗影处下手。爬过棉花田,匍匐在绿豆秧子里,刚想再前进,却被瓜爷拎着耳朵站了起来。别辩白,瓜爷听了不高兴,“生瓜梨枣,揪个就跑”。和先前一样,提溜着土篮转一圈,每个小小的梦里就有了甜瓜的馨香 。
十年前回家,瓜爷的瓜田不见了,那口汲取香甜的老井,也已垮塌在岁月的流转里。一方深陷的大坑,坑里的草,葳蕤丛生,一直爬上了不远处的一座孤坟。不,那是瓜爷和瓜奶的家。听老村长说,瓜爷活了一辈子,就一个念想,阳世里“瓜田李下”,阴世里也好有个暖心的伴儿。
离开瓜田,脚步竟沉沉的,抬不动脚跟。怕是瓜爷又在叫了吧――“一人俩,别吃独食”,一阵香甜就钻进心窝子 。我知道,是瓜爷种了一生的香甜,再次濡湿了我的眼睛……
三、只记得那年枣如雨
“七月枣红圈儿”,只是还未走出雨季。村前有片枣树林,挂满了青的、红的、半青半红的枣儿。长如拇指且有指节的叫“长虫枣儿”,长长的果,长长的核,像是挂满了树的铃铛。圆溜溜大如牛眼的是“核桃纹子”,嚼在嘴里发木,甜得也不地道,但适合做枣花馍,年除夕供到年十五,甜得馥郁。脆如梨的叫“脆铃儿”,单听名字就脆脆生生,丢进嘴里就像含了一团蜜。
铃儿最喜吃“脆铃儿”。铃儿是我的小友。
铃儿与我同岁,扎两个小羊角辫儿,常跟屁虫样跟着我,捉鱼,点火,小河滩上去放羊。那时已九岁,意识里是铃儿挡风的一面墙,小手叉腰,喝退几个顽皮的小子,就换来一天“小家家”的快乐时光。所以铃儿叫我哥,脆生生就像嚼了一颗“脆铃儿”,美得梦里还直应声。
小时候淘,是天性,虽不说“上房揭瓦”,却也练就一身爬树的轻功。甭管直冲云天的钻天杨,还是满是刺蒺的老槐树,更不用说枣树了你是我最美的时光免费,单看见那一树树的青青红红,脚底板子就抓心似的痒,哧溜儿就蹿上了树梢。然后憋红了小脸使劲摇,噼里啪啦,满天就下起了枣雨。
“下枣雨喽!下枣雨喽!”铃儿就在树下伸开双臂,摇晃着羊角辫儿,陶醉地呼喊。枣如雨,打在刚下过雨的水汪里,溅起的水花,晶莹无比,笼罩着快乐的铃儿……
午饭后,还没走到枣树林,远远走来一群人――有铃儿娘惨痛的哭声,老会计牵着一头老牛你是我最美的时光免费,铃儿软绵绵地搭在牛背上,羊角辫儿散开,光着小脚丫,浑身湿淋淋,“啪嗒、啪嗒”滴着水,滑过老牛金色的皮毛,留下一道道泪般的痕……
铃儿是在那颗“脆铃儿”树下溺水的。老会计看见一块小花布在水里漂,用筢子一耙,铃儿已经停止了呼吸,手心里还攥着一颗“脆铃儿”枣,一半青,一半黄,不到成熟的时节。
跟着人群,跟着铃儿,跟着那头驮了铃儿的老黄牛,知道了什么是泪水。苦苦涩涩,顺着嘴角,一路流到心里。
从那天起,再也不吃脆生生的“脆铃儿”,怕泪水把心硌疼。那片青青的枣树林也随着岁月老去,不知能不能走进铃儿的梦里,慰藉那还未串红的孤独。
那年枣如雨,纷纷扬扬,心碎在一个没有结局的雨季……
四、田埂子啊飘呀飘
在这里,田埂子相当于地界,比田里的垄宽些。毗邻的两家常不去动它,任由田埂子上长满青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一年年在黄土地上飘呀飘。
黑大和玉林家搭界,当然共一条田埂子。
玉林家姐弟四个,七几年爹就患上了偏瘫,别说干活,连大小便都成了问题。家贫难度日,玉林娘操持完家务,还要去侍弄庄稼,姐弟几个像是没人管的娃儿,自生自长自开花。
小时候不懂,放学回家的玉林常见黑大在自家地里忙活,娘也在,一个南一个北,光顾干活也不拉呱。玉林就问:“黑大家的田在那边啊,你看他家田里的草就长过了庄稼,为啥还给咱干活?”娘不说话,望一眼在远处的黑大,叹了口气,在飘动着满眼青绿的田埂子上坐下。
黑大有老婆,前村“神婆”刘三娘家的闺女,生得健硕,甚泼,记忆里老打玉林家门前指桑骂槐地走过。黑大黑着脸,“整天价骂街,也不积点阴德,这辈子生不下娃来,下辈子还是绝户……”
慢慢长大了,村里常有风言风语传到玉林耳朵里。“那黑大家也有田,却一年到头春种秋收老往别人家田里跑,到头来,自己家的粮食还管不饱肚皮呢,图希个啥?”三五长舌妇撺掇在一起,讲得唾沫星子乱飞。玉林不得不憋红了脸匆匆而过,他要回家问问娘,是不是娘和黑大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玉林挨了娘的耳光。平生第一次打了儿子的玉林娘泪落如雨,娘说:“林儿,记住,娘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黑大也是好人。好好上学吧,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是为啥。”
农忙时节,玉林家田里依然有黑大忙碌的身影,玉林娘仍和黑大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黑大老婆还是想起来就练练嗓子,村里的闲妇有空还是唾沫星子乱飞,不变的还有玉林家和黑大家之间的那条田埂子,过了十几年,依旧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像一条美丽而柔软的带子飘呀飘。
九几年,玉林参加工作了,弟妹们也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玉林发誓,一定要把爹娘带离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乡村,他忘不了那些刻薄的面孔,也忘不了那些刺耳的声音。
那一天,一家人都在,躺在床上二十几年的父亲竟慢慢从床上挪下来,用含混不清的话语示意娘。娘出门去,回来时跟来的除了黑大还有他老婆。娘说话:“林儿,你们给你黑大和黑娘跪下。”面面相觑,谁都没有动。玉林爹抽搐着嘴唇:“跪下!”含混却极具威慑力。姐弟四个极不情愿地跪下,娘的哭诉和着泪水喷涌而出――“你黑大照顾了咱家二十几年,只因为和娘相过一次亲。刘三娘作梗,说娘命硬是灾星,然后把你黑娘许给你黑大。你爹躺下时,你们几个还小,娘身子弱,全仗你黑大才算顾得上温饱,自己家却常揭不开锅。林儿,你明天找上老队长到田里去看看,一块田,百余丈,咱家足足种了你黑大家一亩七。那条田埂子在他家田里二十几年,你算算,不算出力,咱家吃了你黑大家多少粮食……”
玉林家搬走了,地契上写着:所有田地全托付黑大经营,包括老宅基,包括大树小树所有树……
如今,那条田埂子依然在,春去秋来飘呀飘,飘在每个人的心里。
五、活在童话里的村庄
村子不大,村东说话,村西答腔。有赊小鸡的,“赊小鸡喽……”“喽”刚出来,“赊”还在天上飘。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爬树,偷瓜,捅马蜂窝,被蜇了跑去村口的小庙里,把香灰用唾沫和了,敷在包上。不疼了,大略是玩得疯,忘了。跪在神像前,磕头如捣蒜,“谢谢菩萨奶奶,顺便把爹的鞋底也变成烧饼吧。”当然,这是心里话,别说烧饼了,能捧个大白馒头,也是唯一的奢望。
疯累了,玩够了,一窝蜂跑到小脚六奶家里听故事,听山伯英台双双飞,也听莺莺思念张生夜垂泪。六爷是民国时期的老会计,一手狂草写得龙飞凤舞,六奶原来是小城一官宦家的千金,就冲这狂草,扛个小包袱,嫁到了小村。六奶也写字,蝇头小楷,记忆里工工整整抄录过《聊斋志异》,然后讲给小孩子们听,眉眼神秘,一张一弛,就系住了一个个小小的胸膛。一开始还怕,怕《画皮》里的长舌吊睛女鬼深夜靠近窗棂,后来听得多了,知道鬼狐里也有像“陆判”一样的好“鬼”,就熄了油灯,希冀着也能从某处袅袅走来“颜如玉”或者“小倩”的身影。
书里的鬼鬼仙仙,离得太远,听多了感觉太飘渺,而对于“泰山姑娘”庙,六奶有一种说不出的虔诚。六爷在文革的时候死了,没有子嗣的六奶就住在一所废弃的教堂里,六奶明知道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神仙不是一伙的,但因为教堂里早已没有了十字架的气息,也不在意。抑或六奶根本就把自己当做了乡间的修女,初一十五,收拾整齐,发髻上缠一朵素雅的绢花,颠着小脚,出教堂,去了“泰山姑娘”庙,双膝跪倒,口中喃喃有词。像是许愿,又像是在传递着中西教义里某些相通的东西。
关于“泰山姑娘”庙的来历,当然也是听六奶说的,时值很久远的一场水灾。
一整个夏日,村子都在水里泡着,房子,院墙,该塌的塌了,不该塌的也摇摇欲坠。田地里,麦子已经大片大片地死亡,黑乎乎,像无边的深潭。
六奶的六奶,也就是六爷的六奶,眼看着没有了活路,发了疯似的泅着水去了村前的小河。浊流滚滚,六奶的六奶渐渐淹没了头顶。当时六爷年纪小,就哭,哭晕了,再醒来,六奶的六奶坐在一块石碑上面色红润地发呆,碑无字,六奶的六奶嘴里兀自咕哝着:“我本泰山一清姑,大水漂石尔众福。”水就慢慢退了,退了水的村口后来立着那块漂来的石碑。重新活过来的六奶的六奶,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神婆,小儿夜哭,猪牛远游,一道神符烧了,再包些香灰水服,每每灵验。
当然,这也是听六奶说的,也是我听过的关于“泰山姑娘”来历最完整的一个版本。现在若问及村里最老的三爷,他必斜了面瘫的嘴说:“老辈子有个人坐在河边洗衣裳,一阵乌云来,一阵狂风起,远处飞来一只硕大的黑蝴蝶。蝶有金光环绕,飞过芦苇荡,绕过槐树林,落在了青石小桥上。然后那个人魔怔般站立,回头,目光呆滞地向村子里走,到了现在小庙的地方,凌空传来一句袅袅的清音――我本泰山姑娘,临此荫护族人。”
大约是这样的吧,三爷无头无绪地说完,说要回家磨刀杀鬼子。三爷有些老年痴呆。
我去了那座仍有一块无字石碑的小庙,小时候被误做菩萨奶奶的“泰山姑娘”依然清晰。只是当目光落在业已斑驳的石碑上时,兀然一阵惶惑,难道小村就是这样一直从童话里走来的么?风风雨雨,没起高楼大厦,也没惊天动地的奇迹,每个人都在播种着一块生时收获,死去相伴的土地。夜幕,升起炊烟,黎明,唤醒鸡鸣,然后,沉沉地走进下一个梦境,无论是顺流而下的传说,还是横空而来的神秘,都不愿轻易说破。
也许,活着不仅仅就是活着,村庄被童话美丽地包围,只为怡然在浩淼的红尘。歌几番春夏秋冬,醉一回前世烟云,把泪注进沟沟坎坎的土地,长一些青青黄黄的日子。
来源【励志网】自媒体,更多内容/合作请关注「辉声辉语」公众号,送10G营销资料!